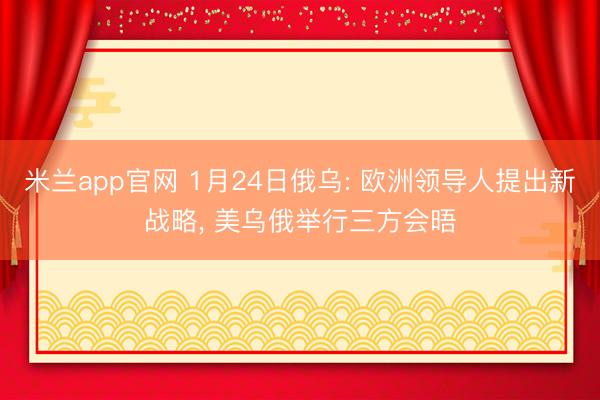1946年,上海,一场私人局。
梅兰芳端坐在席间,面前摆着一只酒杯。
熟悉他的人这会儿手心里都捏了一把汗——为了护着那条价值连城的嗓子,梅先生平日里可是出了名的“四不沾”:不沾辣、不沾酸、不碰白酒、也不碰黄酒。
可偏偏今天,他对面站着的是要回四川的大画家张大千。
张大千举杯大笑:“梅先生,你是君子动口,我是小人动手!”
梅兰芳听完也是一笑,端起那杯平时绝不碰的烈酒:“那君子小人一起干杯!”
这一杯下去,喝的不光是交情,更是狠狠砸碎了一个盘踞在现代人脑子里的刻板印象:民国的上流社会只喝黄酒,白酒那是穷人喝的。
要是真按这逻辑,梅兰芳这一杯,难道是自降身价?
要想把这误会解开,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拉,拉到民国元年。
三十四年前的一组数据,早就把答案摆在那儿了。
1912年,民国刚开张,百废待兴。
这一年,农商部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酒类产量调查。
这份尘封的档案,就像一把手术刀,精准地切开了那个时代的消费肌理,把“谁在喝什么”这个问题,剖得清清楚楚。
数据这东西是冰冷的,但它绝不说谎。
调查报告显示,1912年全国酒类总产量大概是903万吨。
剩下的呢?
烧酒产量460万吨,高粱酒产量337万吨。
这两项加一块儿,就是咱们今天说的“白酒谱系”,总计约797万吨。
这得是个什么概念?
在民国刚开局的版图上,白酒的产量是黄酒的九倍,接近十倍。

要是把当时的酒坛子排成一列,十坛酒里,只有一坛是温润的黄酒,剩下那九坛,全是烈火般的白酒。
为什么会这样?
难道是民国人舌头粗,不懂风雅?
根本不是。
这背后是一笔极其理性的经济账和地理账。
在那个交通烂得一塌糊涂、仓储条件简陋、到处兵荒马乱的年代,酒精是一种需要长途跋涉的商品。
黄酒这东西娇贵,度数低,容易变酸,运输成本高得吓人,还得温着喝,这就注定了它只能在江南富庶的地方、在安稳的席面上偏安一隅。
它是那一小部分城市、一小部分阶层里的“主角”,但绝不是全国的“底盘”。
反观白酒,也就是蒸馏酒。
度数高,耐储存,不怕颠簸,单位体积的酒精含量高,运输效率极高。
在北方凛冽的寒风里,在码头工人的汗水里,在军队的行囊里,甚至在偏远乡村的杂货铺里,白酒凭借着极强的生存能力,铺满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。
黄酒确实占据了审美的制高点,但白酒,实实在在地占据了生活的制高点。
一提民国喝酒,大多数人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画面,往往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。
那温吞吞的黄酒,似乎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落魄或者风雅的标配。
于是,网上就流行起了一种论调:上流社会喝黄酒,下里巴人喝白酒。
可要是咱们跳出小说,去看看真实的鲁迅,就会发现这论调有多荒谬。
真实的鲁迅,绝不是只盯着绍兴黄酒的遗老,他是个口味宽杂、极具生活烟火气的“酒徒”。

在酒友的回忆录和鲁迅自己的日记里,啤酒、黄酒、白酒,他来者不拒。
尤其是白酒。
在上海定居那会儿,鲁迅常干的一件事,就是让人去买“白干”。
注意了,他买的可不是什么精美包装的陈年佳酿,而是“十个铜子的白干”。
这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、最普通的烈性酒。
鲁迅喝它,不是为了什么仪式感,也不是为了品鉴,纯粹就是为了过瘾,为了在写作累了的时候解解乏。
这就有意思了。
鲁迅是谁?
如果白酒真的带着“穷人”、“低级”的阶层羞耻感,像鲁迅这样极其爱惜羽毛、对旧俗极尽讽刺的人,怎么会把“劣质”的白酒当成日常口粮?
唯一的解释就是:在当时,白酒压根就没有被贴上“底层”的标签。
它只是一种口味的选择,一种生活方式的差异。
对于鲁迅来说,喝黄酒是乡愁,喝白酒那是生活。
那种辛辣的口感,或许比温吞的黄酒更能刺激他那支像匕首投枪一样的笔。
京剧名旦程砚秋,舞台上是娇滴滴的旦角,生活里却是个豪爽的酒客。
程砚秋不光爱喝白酒,而且喝出了门道,喝出了境界。
在他的日记里,甚至记录了他“自制白干”的过程。
想象一下这画面:一位享誉全国的艺术大师,在练功演戏之余,亲自研究蒸馏技术,捣鼓白酒的酿造。
如果白酒是“不得已的廉价替代品”,程砚秋这么干,岂不是自降格调?
显然不是。

在程砚秋眼里,白酒是一种值得玩味、值得投入精力的雅趣。
这种对白酒的推崇,在真正的豪门大院里,表现得更露骨。
电视剧《大宅门》里的白家,原型是著名的北京同仁堂乐家。
导演郭宝昌,就是在这个大宅门里长大的“少爷”。
据郭宝昌回忆,他做少爷的时候,十四岁就开始接受“饮酒训练”。
家里长辈教他喝的,不是温润的黄酒,而是茅台这类名贵白酒。
这可不是那个年代的“未成年人饮酒问题”,而是一种严肃的家族教育。
在乐家这样的顶级豪门看来,能喝烈酒、会品烈酒,是男人进入社交圈的一项必备技能,是门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。
在这里,白酒不仅不低级,反而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。
更深一层的逻辑在于,同仁堂是做药的。
咱们要知道,中医药体系里,酒是“百药之长”。
而这个酒,往往指的就是高度数的白酒。
许多采访资料都提到,同仁堂著名的“绿茵陈”药酒,底子就是白干这类白酒体系。
因为只有高浓度的酒精,才能有效地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萃取出来,才能让药力行遍全身。
在当时的城市生活里,白酒不光是餐桌上的饮品,它还嵌入了医疗、养生、送礼这些更广泛的消费结构里。
它是药引子,是消毒剂,是社交润滑剂。
同仁堂的少爷喝白酒,喝的是家族的根基,喝的是对这种“百药之长”的掌控力。
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1912年那个悬殊的产量对比。
白酒,是整个社会运转的润滑油;而黄酒,更像是锦上添花的那朵花。
再回到1946年那场宴席。
为什么平时滴酒不沾的梅兰芳,愿意陪张大千喝那一杯白酒?

除了人情,更因为张大千是四川人。
张大千从小喝着泸州大曲长大。
四川盆地湿气重,不喝烈酒驱寒祛湿,日子都没法过。
对于张大千来说,白酒就是家乡的味道,就是他的“出厂设置”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他在上海设宴,喝家乡的酒,这是地道;梅兰芳客随主便,陪饮烈酒,这是礼数。
它的温润,适合那个“慢”的时代。
但在更广阔的天地里,在日常的餐饮中,在北方的冬夜,在四川的湿雾里,在药铺的柜台上,白酒才是绝对的主宰。
所谓的“上流更爱黄酒”,其实是把“宴席礼俗”当成了“生活全部”,把“江南偏好”当成了“全国通例”。
1912年的那797万吨白酒,不是凭空消失了,而是流进了鲁迅的喉咙,流进了程砚秋的酒壶,流进了同仁堂的药缸,流进了四万万同胞的血液里。
这才是历史的真相。
没有什么高低贵贱,只有适不适合。
它们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滋味——有温润如玉的一面,更有烈火烹油的一面。
白酒从来不是低收入群体的专属,它只是更广泛、更接地气、更能穿透地域与阶层。
当年如此,今天,也是这么个理儿。
信息来源:
《民国农商统计表》,农商部,商务印书馆,1912年(档案数据引用)